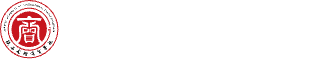摘 要:质量文化蕴含深刻的价值理性,对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具有规约和引导作用。当下质量保障凸显工具理性,存在工具理性的异化倾向。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呼唤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统一、质量保障科层机制和文化机制的共同作用。梳理欧洲高校政策层面和实践层面推动质量文化的经验和做法,对我国高校加深质量文化的认识和拓展质量文化培育具有启发意义。
2019年4月,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在“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启动大会上指出,“文化是最持久、最深沉的力量,打造‘质量中国’,必须建立自省、自律、自查、自纠的高等教育质量文化,将思想、制度、行为、物态等不同层次的质量文化统一起来,营造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氛围,形成全员育人、全过程育人、全方位育人的校园育人文化,把质量意识内化为深入人心的价值理念和行为原则,落实到每一个人、每一件事。”[1] 新一轮审核评估已经拉开帷幕,本轮评估将“推动高校积极构建自觉、自省、自律、自查、自纠的大学质量文化”作为评估指导思想的重要内容,将“培育践行高校质量文化”作为评估基本原则的重要方面,将“质量文化”同时作为第一类和第二类评估的二级指标。[2] “质量文化”出现在评估方案,并在评估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指标体系中如此强调,在我国院校评估中尚属首次。高等学校在内部质量保障中为什么和怎样加强质量文化建设,是学术和实践层面必须回答的问题。因此,厘清质量文化的缘起和价值,梳理总结欧洲在政策和实践层面推动高校内部质量文化发展的有益经验,有其必要性。
一、高等教育质量文化的缘起
1951年,现代质量管理学者约瑟夫·M·朱兰(Joseph M.Juran)在《朱兰质量手册》中首次提出质量文化的概念,认为它是人们与质量有关的习惯、信念和行为模式。[3] 到21世纪初期,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活动的蓬勃发展,促使人们深入思考高等教育管理的文化要素,质量文化被引入高等教育领域,并开始受到重视。一般认为,高等教育质量文化是围绕高等教育质量所形成的理念、信念、价值及由此衍生和发展起来的相关制度、行为、惯习、物化载体等有机体。[4] 质量管理和质量保障在高等教育领域备受争议背景下,高等教育质量文化被提出,旨在弥补质量保障和质量管理的不足。质量文化概念提供了非常全面的涵义,除关注技术和权力对质量保障的作用,还考虑大学组织人员的共同价值观、信念、价值、期望和承诺等文化和心理因素对质量保障的作用。[5]
20世纪初,马克斯·韦伯从研究人的社会行动出发,提出了“理性人”假说,即人的行为的发生必须服从一定的目的或体现一定的意义,并将人类的这种理性区分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价值理性是人类在自身实践活动当中对于价值和价值追求的自觉理解和把握。[6] 它以对价值和意义的追问为依归,致力于为行为主体提供一套行动的理念、目标和理想,注重目的而不关心达到目的的手段。[7] 根据高等教育质量文化定义和价值理性的属性,质量文化对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和提升功能的发挥主要依据其价值理性的作用。高等教育质量文化的价值理性从“应是”出发,致力于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价值选择、意义建构、目标预设、理念型构、原则确立和内容界定。
第一,质量文化对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价值理念的建构功能。质量文化之所以重要,说到底是因为价值理性赋予了它确切而独特的价值理念。价值理性不是以 “物的尺度”为基准反映高等教育质量的本来面目,而是以“人的尺度”为出发点来解释、评判质量保障的现实并预设理想的质量保障形式。[8] 质量文化蕴含了高校和教师需要有清醒明确的质量意识的价值导向:高校要真正关注内涵发展、切实保障人才培养中心地位;作为高等教育教学质量保障和水平提升的责任主体,教师要把教书育人作为自己的天职,把用心培育人才作为最重要的工作。质量文化要求高校和教师有强大的自律自查精神:于学校而言,即使没有外部评估与监督也能遵循教育教学规律,严格教育教学管理,维持良好办学秩序,坚持自我批判、自我反省、持续自我改进;于教师而言,教育教学工作中要坚定职业信仰和道德准则,形成自觉且深入研究教学、与时俱进的职业习惯。质量文化把实现高等教育质量实质提升奉为价值选择、目标定位和价值理想,赋予制度以良心,赋予权力以责任,赋予教学以德性;价值理性给质量保障制度和程序注入质量文化的精髓,为高校质量保障标准、结构和流程建构了丰富的价值理念,从而使高等教育质量保障获得价值合理性和制度科学性。[9] 正如欧洲大学协会2015年修订的欧洲高等教育区质量保障标准和指引(ESG)提出的坚持支持质量文化的发展原则和价值理念:一是确定高校为质量保障的责任主体,质量保障责任需要渗透到高校内部各层面;二是支持全体人员参与,倡导领导、教职员工、学生全体人员和外部利益相关者参与质量保障行动;三是重视学术诚信与自由,警惕学术造假;四是坚持学生中心理念,重视教与学的质量,倡导学生中心的教学和评价,对学生培养全过程进行质量监控和保障,为学生提供充足资源和支持;五是重视质量数据的管理,倡导质量信息的公开和使用,且基于信息分析结果进行决策和持续改进。[10]第二,质量文化具有动力供给功能。一种文化要让人们对它抱有信心并成为孜孜以求的目标,首先在于它自身具有明确的能满足人类内心渴望的本质规定,具有直指人心的感召力。质量文化价值理性的最大功用在于:珍视院校自治和学术自由,尊重高校、学术人员和学生是质量主体的客观事实,考虑院校组织的特征和人才培养的专业特性。就是说,高校对质量文化的追求,实际就是对高校自治和学术自由的追求。长期以来,高校过于受外部行政力量的束缚,因此,挣脱外在第三方力量的支配,追求学术自由和自治是高校和教师梦寐以求的希望,质量文化正是对这一期望的回应。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欧洲高校质量文化的提出和政治目的相关,当时欧洲高校普遍面临欧盟委员会和国家政府要求高等教育进行根本性变革的外部压力,面对这种外部压力,质量文化成了高校追求自治的政治工具:一方面回应外部质量评估的要求,另一方面促进内部治理体系完善。[11] 本质上,质量文化的概念是高度政治化的,承载着政策制定者、大学领导和质量保障相关人员的希望,并以这种方式将质量保障重塑为高校核心价值,而不是外部强加的任务。[12] 它反映质量保障理念从质量控制、强调问责和监管,到重视高校自主权、信任和持续改进的转变。[13]
(二)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凸显工具理性
长期以来,质量一直是学术传统的一部分。起初,质量控制主要基于非正式的同行评审和自我监管。随着政府财政紧缩和高等教育规模扩张,政府和公众加强对高等教育的问责,高等教育外部质量保障制度应运而生。以英国为例,20世纪70年代爆发的经济危机对英国高等教育产生冲击,尤其是撒切尔政府推行的新公共管理改革和追求效率指导思想,大学经费被大幅削减。英国政府认为政府应承担起教育质量保障责任,政府基于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HEFC)拨款,成立了教学质量保障委员会(QAC),开展学科评估(Subject review)。为抗衡政府权力介入,英国大学代言人的大学校长委员会(CVCP)成立了高等教育质量委员会(HEQC)开展质量审核(Academic quality audit)。1997年,HEFC与CVCP合作成立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署(QAA),取代QAC和HEQC,开展学科评估和质量审核。从此,英国大学外部质量保障体系正式建立,这一双轨制(学科评估与质量审核并存)外部质量保障体系运行了20多年。[14]
此时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通过科层机制实现保障质量功能,凸显工具理性。“工具理性指通过对外界事物的情况或其他人的举止的期待,并利用这种期待作为‘条件’或者‘手段’,以实现自己合乎理性所争取和考虑的作为成果的目的”。[15] 工具理性具有重视目的、效率、效益的先进性,致力于提供一套达到目的的技术、工具、途径和方式,但存在忽略目的是否正当与合理的倾向。现代科层机制理论创始者马克斯·韦伯认为,科层机制正是建立在规范性和计算性为原则的工具理性基础之上的,以职能和职位进行分工和分层,以等级制、专业化、非人格化为基本特征的政府组织体系与管理体制。[16] 高等教育质量保障自上而下的运行、工具选择、程序设计和制度安排,本质上属于科层等级结构和整套规章制度协调和控制组织活动,正是充分发挥了科层机制的工具理性。体现在以下方面:首先,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工具理性促使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制度化、规范化。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引入工商业领域中基标法、绩效指标等质量保障方法,广泛采用相关政策、评估、审核、认证、排名、绩效指标等中介和手段作为质量保障的技术方式。这样,相对科学的测量方法和工具,将教育“质量”概念转化为可操作的程序,把质量保障活动简化成清晰可操作的步骤,并基于测量和评估结果改进教学和院校管理方式;其次,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工具理性进一步维系了高等教育在现代社会的合法地位,使利益相关者认识到高等教育质量的确定性和重要性;同时,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工具理性促使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权力运行规范化,转变了学术人员在质量界定和形成过程中的权力垄断,确定了利益相关者参与质量保障议程的合法性,从而使传统学术实践考虑社会的利益和需求,一定程度促进高校与社会的互动发展,符合现代社会和高等教育自身发展需要。一定程度上,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工具理性对高等教育质量提升发挥了有效作用。2008年,世界经合组织的出版物宣称,外部质量保障体系发展是过去几十年高等教育最重要的趋势之一。2010年,欧洲大学协会的报告显示,超过60%的受访机构认为,高校实施内部质量保障是过去十年最重要的改变之一。[17]
然而,当工具理性过度膨胀使原本为达到目的而运用的手段将其所指向的目的消解,工具理性异化就产生了。[18] 当工具理性支配一切的时候,结果就是“理性化导致非理性的生活方式”,也就是韦伯所谓的工具理性驱逐价值理性现象,即理性化的吊诡。[19] 工具理性的效率逻辑,导致行为取向往往只注重短期利益,而忽略长远发展,更看不到短视行为可能产生的巨大隐患,这是以工具理性占据绝对主导地位而只谋求眼前利益的必然结果。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层面,科层机制的工具理性过度膨胀带来的问题:一是技术理性支配下,质量保障出现“技术即目的”的异化,评估者为防止高校弄虚作假不断开发和升级评估手段和技术,高校则想方设法弄虚作假以应对不断升级的评估技术,以提高质量为目的而实施的质量评估游离了质量建设这一出发点和核心要旨,使其成为“猫捉耗子”的游戏。二是高等教育质量保障重构了政府、院校、市场与社会的权力关系,高校为了更多的经费和资源,向政府让步部分权力,接受政府制定的各项质量标准,政府实施的繁杂而严苛的绩效指标,对高校施加压力,形成了政府和高校日趋紧张的关系,消费者偏好及社会公众“用脚投票”和舆论导向也是社会和市场获得话语权的方式;在院校内部,行政人员基于外部社会对于质量的功利主义定义,进一步细化学术人员考核标准,并辅以奖惩体系激励和迫使学术人员遵从。如此,教学自由被干涉,学术自主权遭破坏,损害了大学精神,也降低了大学教师的道德责任感。[20] 表现在:高校内部质量保障体系“模式化”、重“评估”轻“改进”;二级院系与基层教师执行力不足,多数学者对现有质量保障体系缺乏热情,认为质量保障是外部强加的负担;忽视信任,基于问责目的,而不是支持和促进高校达到教学的卓越水平。因此,尽管政府花费大量成本却无法得到预期结果,这是科层制在高等教育质量管理中的固有局限。[21]
上述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概念界定显示,两种理性同属一种话语系统,价值理性规约和引导工具理性,工具理性为价值理性的实现提供支撑,二者只有和合统一才能实现最大效用。反之,如果二者呈现背离倾向,则会影响行为主体的当前效益和发展前景。高等教育质量保障需要建立在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协同作用的基础上,实现合理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在关注手段、工具和方法的合理性的同时,必须符合实践主体的目的性;需要科层机制和文化机制的共同作用:科层机制主要是依靠行政命令、制度规范、管理技术等进行质量管理、约束组织成员的质量行为;文化机制主要借助信念信仰、价值共识等激发所有成员参与质量行动的内源动力,达成“文化自觉”。
欧洲大学协会(EUA)提倡的质量文化概念,是旨在永久提高质量的组织文化,认为任何质量文化都基于两个不同元素:[22]一是一套共同的价值观、信念、期望和对质量的承诺(心理方面指理解、灵活性、参与、希望和情感);二是具有明确过程的结构或管理要素,以提高质量和协调努力(指个人、单位的任务、标准和责任)。这正是对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相统一的回应。在有意识发展的质量文化的过程中,自上而下的结构/管理过程和自下而上的文化/心理因素之间应有持续的相互作用。前一种是作为外部和内部法律法规形式表现而形成变革的驱动力,后一种是质量文化发展过程中的支持性措施。[23] 值得指出的是,质量文化和质量保障体系不能等同,质量保障结构体系是质量文化的一部分,质量文化强调组织各成员所共享的价值理念和做法,且由组织各层级的成员共同培育而成。[24] 有学者认为,欧洲大学协会给出的质量文化定义将质量文化与结构要素——质量体系放在一起混合容易造成误解,质量文化中的结构体系既影响质量文化,也是质量文化的表达,但不能成为质量文化本身的一部分。[25] 著名质量管理专家弗兰克·M·格里纳(Frank M. Gryna)曾言,文化不属于技术范畴,但特定的方法和手段有助于形成这种质量文化。[26] 建设大学质量文化过程中,没有质量管理结构和制度层面的支持,心理和文化层面将是孤立和短暂的。强大和可持续的质量文化不仅需要质量保障体系的支持,还建立在教育过程中各方的相互信任之上,也需要时间和空间自主探索,并非自上而下的强制执行结果。同理,没有质量文化的价值理念规约和引领,没有文化意识的渗透,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制度和流程的运行就有落入形式主义的倾向,自发行为只能停留在“我被要求这么做”的浅层次,而不能上升到理性自觉和价值追求的高度。当下,应当在发挥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工具理性价值的同时,致力于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价值理性的回归和重建,以价值理性引导和规范工具理性,实现二者有机统一,促进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可持续发展。
二、高等教育质量文化的发展
高等教育质量文化的发展离不开系列政策的持续推动。2002-2006年,欧洲大学协会支持实施了系列促进高等教育质量文化的项目,包括“质量文化项目”(Quality Culture Project)、“监测高校质量文化”(Examining quality culture in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促进高校质量文化建设”(Promoting quality culture in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授权高校履行质量保障的责任”(Empowering Universities to fulfill their responsibility for Quality Assurance)。系列质量文化项目作为博洛尼亚进程的副产品由欧盟推动,得到了欧洲大学协会的经济支持,旨在提高人们对高校内部质量文化建设重要性的认识,且介绍和推广关于质量文化建设的好的做法,促进高校内部质量保障能力建设,推动博洛尼亚进程。2009年10月,欧洲大学协会(EUA)与其合作伙伴德国校长会议(HRK)和苏格兰质量保障局(QAA)启动了名为“高等教育机构质量文化研究”(EQC)的项目。EQC项目是EUA与其成员在发展内部质量保障方面长期工作的延续。两年半时间里,该项目探索了质量文化发展和质量保障过程之间的动态关系。2012年2月在苏格兰爱丁堡举行最后一次研讨会,来自欧洲大学协会成员高校的30名代表参加了此次研讨会,共同讨论不同高校中发展质量文化的挑战和有效做法。
2015年,欧洲高等教育区成员普遍采用的高等教育质量评估,采用欧洲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协会、欧洲学生联盟、欧洲大学协会、欧洲高等教育机构协会共同协商修订的标准和指南——《欧洲高等教育领域质量保障标准和指南》(简称《ESG2015》)。[27] 《ESG2015》明确其制定过程遵循的四项基本原则之一是质量保障结构体系有助于发展质量文化。可见,欧洲高校把发展质量文化的重要性摆在突出位置且一以贯之地实施。欧洲大学协会2022年高等教育质量保障论坛的主题是“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在促进高等教育基本价值理念中的作用”,倡导利用高等教育质量文化中的结构和心理层面,保障高等教育价值理念的落实,如在质量保障条文中彰显高等教育基本价值观,制定具体的质量保障措施,以支持高等教育基本价值观的落实。[28]
(二)高等教育质量文化的实践推动
发展质量文化具体实践中,影响高等教育质量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因素主要有组织结构、文化心理、领导和参与沟通等四个层面。欧洲不少高校在此四个层面实践中开展了诸多尝试。
1.组织结构层面
质量保障组织结构层面主要通过以下两方面促进质量文化发展:一是质量保障组织和结构本身以暗默的方式传递质量文化,本身其实是质量文化的“外化”,对质量保障主体起激励作用;二是组织结构引导与推动质量文化的生成和发展,质量文化属精神层面,质量保障组织机构属实体层面,质量文化的转化和落地依托系统完善的质量保障组织结构设置。因此,质量保障过程中,要形成结构合理、职责清晰的质量保障结构,包括负责质量管理的领导机构、执行机构、监督机构及其职责划分,加强组织机构的沟通合作、协调配合,厘清各部门质量职责与边界,梳理部门间质量管理工作流程,制定切实可行的制度规范,形成职责明晰、分工协作,各负其责、各自担责、运行顺畅、工作高效的质量管理机制;同时倡导全体人员参与,基于评价结果持续改进,避免形成过于官僚的等级结构、高度集中的质量管理制度。2011年,欧洲大学协会高校质量文化监测项目(Examining Quality Culture in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EQC)调查显示,欧洲绝大部分高校建立了稳定和持久的组织结构以确保质量管理,倾向基于已有组织机构建立质量管理机构和明确质量管理职责以减少工作任务。所有质量保障办公室直接或间接向学校管理团队报告,从而保障独立性;选择能力出众的行政人员和有专业背景的学术人员任职;搭建交流平台,促进全体人员参与质量文化建设,引入质量文化时,配置专门人员解释和推广质量文化。
质量文化突出教学质量的重要性,强调教师保障教学质量的作用,关键是从文化心理维度改变教师对教学的价值认同和理想信念。其中,学术认同感和学术自由是核心要素,任何教学改革都需要基于教师自发承诺,否则教师只是形式上遵守改革的规定,不会实质性参与其中。教与学学术化(Scholarship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是改变教师学术认同和学术信念的重要方式,是促进质量文化在教与学过程中渗透的有效路径。教与学学术化基于明显的理论框架,对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系统观察和分析,包含记录过程并将结果公开供同行评议。社会文化视角下,教与学的学术化强调教与学的文化属性,不仅为了促进个人提高,也旨在建设质量文化,整体上促进师生重视和不断改进教学质量。
以瑞典隆德大学为例,为促进教学改革,提高教师学术认同感和学术自由,坚定教师教学理想和信念,促进质量文化发展,该校主要通过以下方面实施教与学学术化:一是提供教学类课程。20世纪70年代以来,隆德大学一直为教师提供教学课程,课程是基于学生学习理论的专业教学实践反思。20世纪90年代以来,建议教师在受聘两年内完成为期10周的培训,随后将该类教学课程定为教师的必修课。二是项目汇报。教学课程中,教师需要反思教学经历,并选择一项和教学实践相关的课题展开研究,形成汇报。这些报告为后面的参与者提供灵感,同时也对报告进行元分析,找出教师在教与学学术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为学校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三是“批判性朋友”。“批判性朋友”概念模型经常用于处理教学课程中的问题,有利于打造学习共同体。[29] 当事人向自己的一位朋友提供课程报告,根据文本提出的观点与结果和朋友讨论,讨论结果附在文本中,作为教育学课程考试作业的一部分。[30] 四是院系研讨会。院系研讨会由教师向部门同事介绍他们的研究课题。研讨会以教育理论为基础,基于学科教学范畴,支持正规形式探讨,加深教师理解教学实践。五是学校教学会议。学校每两年举行一次教学会议,会议有论文征集,根据相应标准同行评审论文,会议过程记录发布于大学网站。六是奖励方案。奖励给予个别教师和教师所在院系。获奖教师参与学术讨论、会议和出版书籍,公开其教学经验。七是升职要求。目前,隆德大学更加关注申请人对教学实践的学术反思和参与教学改革的能力。近年来,一些寻求晋升教授职位的申请者缺乏教学学术能力而不予通过,这一规定直接促进了有经验的教师参加教学课程的兴趣。八是质量文化形成的证据。一项独立的国家评估证明了教与学学术化的开展促进了隆德大学质量文化改变。[31] 评估调查了瑞典五所高校(包括隆德大学工程学院)参加教学课程的1100名教师。以往研究显示个别教师即使参加了鼓舞人心的教学课程,但一旦回到自己的部门,会面临同事缺乏兴趣甚至产生敌意的困境,使其难以实施改进教学的想法和实践。[32] 而在隆德大学工程学院,经历了系统的教学改革后,教师个人参与程度、参与者实施教学改革后同事之间的支持都表明,教与学学术化促进学术共同体的形成,提升了教师的学术认同和部门的教学质量文化。[33]
3.领导层面
诸多实证研究表明,领导对质量文化发展起关键作用。有效的领导者能胜任激励者、愿景设定者、任务主持者和分析者等多种角色。领导者能解决组织结构和管理维度的阻碍因素,影响资源分配,明确角色和责任分配,创造信任和共同理解的文化氛围。欧洲大学协会总结了40个国家的近300所高校嵌入质量文化的有效做法,肯定了领导推动质量文化的关键作用,可从以下方面具体发挥作用:一是制定质量管理的整体策略并协调实施,明确各角色的职责职能。质量管理战略及策略和高校自身目标和定位一致,可采用SWOT方法,分析高校的优势、不足、机会和威胁,明确高校的短期、中期和长期目标,建立质量管理战略;二是推广和传播质量文化,建议将质量文化的推广纳入副校长的责任;三是协调和满足员工需求,将学术人员和行政人员纳入高校质量决策过程,善于倾听师生和全体员工需求。如促进教与学学术化过程中,领导者要对教师的需求保持敏感性,倾听教师意见与建议,必要时改变和制定规则,支持教师教学质量的提升。[34]
尽管质量文化强调不同利益相关者的沟通和参与,但对如何吸引利益相关者参与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仍没有提供实际解决方案。换言之,质量文化把利益相关者参与质量保障放在重要位置,但也要求具体落实利益相关主体的参与和沟通。
欧洲大学协会通过总结高校推动质量文化实践,发现一些困境并实施了相应解决路径。
首先,在参与方面,组织的每个人,不仅仅是质量控制人员,都要对质量负责,每个参与者都朝着共同目标努力,质量控制人员只是调节相关过程。但很快发现,尽管所有人都雄心勃勃地将质量保障体系重塑为高等教育机构的核心价值,而不是强制执行的任务,但多数质量保障活动都是固有的自上而下的实施逻辑。当师生被邀请参与并承担责任时,通常多数规定已明确设定。换句话说,利益相关者被要求参与过程甚至被要求对其结果负责,而并不拥有过程的制定权。为解决利益相关者参与问题,欧洲部分高校从以下方面尝试:一是培养责任感(commitment)。如果教职员工的价值理念和组织一致,教职员工责任感便会增强;如果教职员工能参与组织决策的机会较少,教职员工对组织的责任感也会较弱。因此可让师生代表共同商讨和决定质量保障过程的规定和标准,监测其实施的有效性,对质量保障结果负责。二是增进了解(knowledge)。教师了解教育计划、策略和目标,明确工作任务、责任,明白质量文化建设需要付出的代价和质量文化所带来的价值。[35] 可聘请相关专家提供培训,增进师生对质量文化的理解。[36] 利益相关者参与质量保障相关研讨会时有不情愿的情绪。多数质量保障政策和过程似乎很难摆脱给师生带来额外负担的形象。因此质量保障过程中,需要解释关键概念和专业术语,并转化为参与者的日常语言,让参与者在熟悉和擅长的领域做出贡献,而不是要参与者对质量保障体系做全面的了解。三是赋权(empowerment)。赋权不同于参与,参与指教师是组织的一部分,能参与政策的决策过程并献言献计。员工参与只是赋权的一个过程[37],赋权意味着把控制机制下放给工作人员。如保障教师在决定教学方法方面有足够自主权,重视和采纳教师关于提高学术质量的建议等。其次在沟通层面,每个组织都依赖于沟通建立信任,实践中,沟通常被忽视。常见交流模式仍是简单将信息从发送方传递给接收方,而不是具有协商意义的双向过程。多数质量保障体系都强调反馈,但仔细观察,会发现沟通只是单向性。如学生和毕业生填写调查问卷并提供反馈,这个循环很少以透明的方式呈现。如何处理反馈的信息,即使是教学人员也很少知道,因此有必要强调沟通机制的双向性。信息监测和共享是沟通的重要方式。高校要重视监测质量的过程和监测结果的利用,确保信息监测过程和结果具有明确的支持和效用,避免监测过程沦落为控制机制。监测信息指标设定时,定性和定量指标结合,基于清晰的目标搜集相关数据,防止信息搜集任务过重,给教职员工造成不必要负担。建立质量监测平台和大数据分析平台搜集、传递、联结和共享数据。诞生于工商业领域的质量保障技术与工具并不完全适用于高等教育,高等教育以人才培养为核心,其质量不是一种物的客观存在,更多的是一种精神性的东西,是一种文化的结晶。[38] 理论上,质量文化对质量保障具有重要作用。现实中,高等教育质量的保障和提升往往依靠技术和资源的投入,质量文化的价值往往不受重视或无法实现。我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价值理性尚未良好显现,高等教育质量保障需要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协同作用,需要重视价值理性的规约和引导作用,发挥质量保障技术与质量文化统一。要避免质量文化建设沦为形式主义,而无法深入组织师生员工的心灵深处。参考文献
[1]陈宝生. 掀起一场高等教育“质量革命”助力打造“质量中国”——在“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启动大会上的讲话[EB/OL].[2022-11-25].http://jiaowu.xaufe.edu.cn/info/1081/2658.[2]李志义,朱泓. 以先进的质量保障理念促进本科教育教学综合改革[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21(6):75-80.[3]约瑟夫·M·朱兰,约瑟夫·A·德费欧. 朱兰质量手册[M].第六版.焦叔斌,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4]别敦荣,易梦春. 高等教育质量文化及其建设策略[J].高等教育研究,2021(3):7-16.[5]DZIMIMINSKA M,FIJALKOWSKA J,SULKOWSKI L.Trust-based quality culture conceptual model for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J].Sustainability,2018(8):1-22.[6]韦伯. 经济与社会:上卷[M].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56.[7]伯特兰·罗素. 伦理学与政治学中的人类社会[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25.[8]王彩云. 民主化进程中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功能探析[J].江汉论坛,2014(5):33-37.[9]HAVRVEY L.Quality culture,quality assurance,and impact.Overview of discussions[EB/OL].[2022-12-20].https://www.qualityresearchinternational.com.[10][27]ENQA.Standards and Guidelines for Quality Assurance in the European Higher Education Area(ESG)[EB/OL].[2022-12-20].https://www.enqa.eu/wp-content/uploads/2015/11/ESG_2015.pdf.[11][22][23]HAVRVEY L,STENSAKER B.Quality culture:understandings,boundaries,and linkages[J].European journal of education,2008(4):427-442.[12]VETTORI O A.Clash of quality cultures:a conflicting and coalescing interpretive patterns in Austrian higher education[D].Austria:University of Vienna,2012:4-37.[13]JENSEN H T,ASPELIN M,DEVINSKY F,et al.Quality culture in European universities:a bottom-up approach[R].Brussels,Belgium:European University Association,2006:2-24.[14]李志义. 紧紧牵住“牛鼻子”审核评估就不会“跑偏”[J].高教发展与评估,2013(5):111+101.[15]韦伯. 经济与社会:上卷[M].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56.[16]王彩云. 政治学视域中价值理性的回归[J].政治学研究,2013(6):94-103.[17]NEWTON J.Views from below:academics coping with quality[J].Quality in higher education,2002(1):39-61.[18]陈新汉. 论价值理性及其异化[J].学术界,2020(1):45-55.[19]杨善华,谢立中. 西方社会学理论:下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88.[20]张应强,苏永建. 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反思、批判与变革[J].教育研究,2014(5):19-27+49.[21]李志义. 新一轮审核评估方案设计与实施要点[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21(3):9-15.[24]VETTORI O.Examining quality culture part III:from self-reflection to enhancement[R].Brussels,Belgium:European University Association,2012:12.[25]VANJA PEROVSEK.The quality culture paradox and its implications – is there a way out[EB/OL].[2022-12-17]. https://eua.eu/downloads/publications/.[26]弗兰克·M·格里纳. 质量策划与分析[M].何桢,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28]CRACUIM D,MATEI L,POPOVICI M.A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fundamental values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quality assurance[M].Strasbourg:Council of Europe,2021:55-65.[29]HANDAL G.Consultation using critical friends[J].New directions for teaching and learning,1999(79):59-70.[30]武晓蓓. 论批判性朋友[J].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3):32-38.[31]GRAN B.Pedagogical courses for academic teachers:an evaluation of a pilot project[R].Lund:Lund University,2006:238.[32]ENTWISTLE N,WALKER P.Strategic alertness and expanded awareness within sophisticated conceptions of teaching[J].Instructional science,2000(28):335-361.[33]MARTENSSON K,ROXA T,OLSSON T.Developing a quality culture through the scholarship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J].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 development,2011(1):51-62.[34]RUED’EGMONT R.Quality culture in European universities:a bottom-up approach[R].Brussels,Belgium:European University Association,2006:1-42.[35]KLEIJNEN J,DOLMANS D,WILLEMS J,et al.Does internal quality management contribute to more control or improvement of higher education?A survey on faculty’s perceptions[J].Quality assurance in education,2011(2):141-155.[36]KANJI G K,MALEK A,TAMBI B A.Total quality management in UK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J].Total quality management,1999(1):129-153.[37]SAHNEY S,BANWET D K,KARUNES S.Quality framework in education through the application of interpretive structural modeling:an administrative staff perspective in the Indian context[J]. The TQM journal,2010(1):56-71.[38]王建华. 高等教育质量管理:文化的视角[J].教育研究,2010(2):57-62.